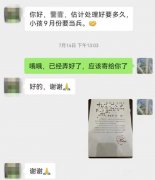直播回顾:民谣中“南方”“北方”意象增多,源于地域性的消解
2012年,一首《理想三旬》让唐映枫以词作者的身份走进大众的视野。直到今天,依然源源不断地有人被这首歌所打动,希望听他讲词作背后的故事:网络投稿,音乐人征用,趁着女朋友喂鸽子的间隙写完后副歌部分——这样的情节,他已经在不同场合复述了很多遍。《理想三旬》成为唐映枫的代表作和标签,他不拒绝,“自己做错的事要承担,嗯,开个玩笑”。
就老去吧,孤独别醒来
你渴望的离开
只是无处停摆
——《理想三旬》
唐映枫,独立音乐人,枯鱼肆音乐工作室创始人,传记代表作《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》《鱼干铺里》《硬骨见鹿集》《鸟的世相》等。
8年过去了,唐映枫已经成为了发表过上百首词作,身兼作者、歌手、制作人、厂牌主理人等多重身份的职业音乐人。他的创作也不局限于童年和故乡,还有多元的亚文化和绚丽的想象。今年他出版的杂文集《六日改》,收录了他这几年创作的歌词、诗、短句和杂文,零星的创作碎片组合成了一个更加多面的唐映枫。
7月,唐映枫带着他的《六日改》来到新京报·文化客厅的直播间。“直播太别扭了。”他反复说,“你看到有人在回复你,想跟他们对话,但对面并没有人。”相比较“梦倒塌的地方,今已爬满青苔”(《理想三旬》歌词),“小炒无剁椒何以度秋”(《六日改》收录短句)式的生活感更接近唐映枫本人给人的初印象。他说小时候不听流行情歌,只想抓数码宝贝和神奇宝贝;读过最多的书是《七龙珠》,看完故事再读分镜;他现在在家读小津安二郎的剧本集,小津生活化的台词令他着迷;他说他之所以叫“映枫”是因为出生在秋天,当时父亲给他取了三页纸的名字;在直播的前一天,他在B站上熬夜看音乐剧《汉密尔顿》……身份之外,他是一个和90后们共享着类似文化记忆的普通人。
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分享,话题涉及流行音乐、民谣、独立音乐,还有创作。他的创作与互联网,以及当下的城市青年生活互为映射。在地域感逐渐消解的今天,流动的生活给广大的城市青年带来了已经反复被讨论的归属疑问,在唐映枫这里他给出的答案是:接受它,但不要忘记与过去的连接。
《六日改》,作者:唐映枫,版本:新民说 |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5月
1
不知道在跟谁对话,
是表达者共有的困惑
新京报:作为音乐人,你并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音乐教育,最开始的音乐熏陶是来自于流行音乐吗?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流行音乐记忆吗?
唐映枫:我记忆中第一首会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《青青河边草》。我还记得96年、97年有一首任贤齐的《心太软》,那个时候我大概只有五六岁,歌词听不太懂,跟着乱唱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,听的更多的是喜欢的动画片的主题曲。
对于流行音乐,最开始我其实不太接受。当时我们那个地方能听到的内地流行音乐大多是情歌,完全没办法带入自己。我成天想的是什么时候能抓到一只数码宝贝和神奇宝贝,谁要听你唱情歌啊。
读初中之后我开始听周杰伦,这有受我哥影响。我哥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住我家,他的起床铃声是周杰伦的《以父之名》。每天早上六点半,《以父之名》高亢的女声前奏就会开始响起,导致我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条件反射式的清醒。其实我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时间要更早,我印象很深,在我爸的诊所里。当时《双截棍》在MTV电台打榜,说这首歌引起了华语乐坛旋风。《双截棍》结合了很多音乐元素,是说唱,当时我还在想怎么整首歌没怎么唱就完了。
到了初一,正是喜欢周杰伦的年纪。因为你终于听到了一些你想在音乐里面听到的东西,比如对异域的描写和想象。所以我对流行音乐的记忆的起点很早,但是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是这个时期。
新京报:那些描写异域的流行音乐如何触发你?
唐映枫:最开始你以为写词是不可触碰的,但是当时和网友聊天(当时已经有了网络音乐)发现原来大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最开始写歌词时你会想找一个参考。那个时候你听不懂罗大佑也听不懂李宗盛,但是周杰伦、方文山那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,会让我对如何写词有一个最初的印象。
新京报:说到网络,在《六日改》中你也有提到,最开始写词时你会把作品发到一个叫“原创歌词吧”的贴吧里。后来你接到第一次歌词合作,包括后来通过网络投稿和陈鸿宇达成合作、因为《理想三旬》走红,一直以来你跟网络有很紧密的联系。那么在你看来,互联网对音乐产业有怎样的影响?
唐映枫:不只是音乐创作,所有类型的创作在互联网平台上都会有更丰富的创作空间。但是在网络空间中,有些创作表达会更加自我,也会让整个市场更加分众化。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在跟谁对话。
新京报: “不知道在跟谁对话”,这会让你困惑吗?
唐映枫:当接触到更多的音乐人之后我发现,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只要是在表达的人,你就会遇到不知道在跟谁对话的困惑,只是在互联网上你会感受得更加明显,而且很快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反馈。
新京报:会想改变吗?
唐映枫:改变不了吧。
新京报:现在如果有人再让你去评价林夕、李宗盛,你会做何反应?
唐映枫:为什么让我去评价别人呢(笑)。可能说明词作人还太少了吧,只要出来一个词作人,就会让你去跟之前的作比较。其实虽然看上去在做同一件事情,但是我们的创作理念、合作经验都是不同的,做评价不应该是我们去做的事情。
《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》专辑封面
2
民谣中的“南方”“北方”,
体现了当下被消解的地域性
新京报:现在人们提到你,都会给你贴上“民谣”的标签。我们来聊聊民谣这个音乐类型吧,你觉得现在的民谣跟上个世纪的民谣有区别吗?